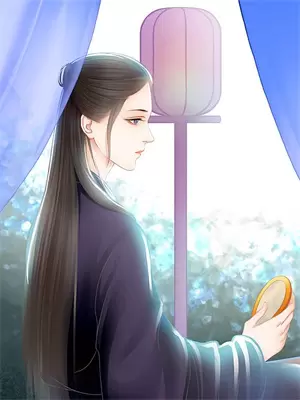在我妈忌日当天,谢予舟带人闯进我家,砸了她的牌位。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个灾星,
只会带来厄运。“跟你在一起七年,我做什么都失败,白若曦才是我的福星!
”他当着所有亲友的面,宣布和首富千金白若曦订婚。我被净身出户,流落街头,
当晚就发起了高烧。再次醒来,我能看见每个人身上的“东西”。谢予舟和他全家,
都被浓郁的黑气缠绕,黑气中伸出无数只惨白的手。而他那位“福星”未婚妻,
身后跟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婴灵,正对着他诡异地笑。他生意破产,全家怪病缠身,
终于想起我这个“灾星”。他跪在我的出租屋门口,磕头磕到流血。“阿寻,我错了,
求你救救我,救救我们家!”我看着他头顶盘旋的、最浓郁的那团黑气,笑了。“救你?
可以啊,你从这三十楼跳下去,我就告诉他们,你是为我殉情死的。”1.高烧退去的时候,
窗外正下着雨。雨水敲打在医院玻璃窗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睁开眼,世界变得很不一样。
护士走进来给我量体温,她的肩膀上,趴着一团灰蒙蒙的雾。雾气很淡,像抽剩下的烟。
我眨了眨眼,那团雾还在。护士皱着眉,一边记录一边抱怨着肩周炎又犯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办完出院手续,我口袋里只剩下几百块钱。净身出户,谢予舟做得够绝。
我在医院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日租房,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房东太太领我进去的时候,
我看见她的小腿上缠着几缕黑线。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嘟囔着老寒腿,天气一变就疼。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这不是幻觉。我真的能看见了。看见那些盘踞在人身上,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在小旅馆里待了三天。三天里,我透过窗户,
观察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一个刚中了彩票的男人,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一对正在争吵的情侣,被一团焦躁的、不断碰撞的灰气笼罩。一个刚丢了钱包的女孩,
头顶飘着一小片乌云。我好像,有了一种新的能力。在被谢予舟抛弃,砸了我妈牌位,
一无所有之后。这算什么?老天爷的补偿吗?我扯了扯嘴角,笑不出来。
我租下了一个老小区的顶层,一个月八百。房子很破,但阳光很好。我把剩下的钱拿出来,
请人重新做了一个牌位。这一次,我用我自己的钱。牌位立好的那天,我看着妈妈的名字,
心里那块由背叛和屈辱凝结的冰,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妈,我没事。我会好好活下去。
2.我找了一份在餐厅后厨洗碗的工作。很累,薪水也低,但至少能让我活下去。
每天油污满身,回到那个破旧的出租屋,累得连指头都不想动。我没时间去想谢予舟。
也没时间去恨。直到一个月后,我在餐厅里,看见了谢予舟的妹妹,谢玲。
她和几个朋友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我没见过的当季新款。还是那么骄纵,那么不可一世。
她曾经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有点自知之明,别拖累他哥”。我低下头,正准备躲进后厨。
视线却凝固了。谢玲的身上,缠绕着一缕极黑的雾气。那黑气中,有一只很小的、惨白的手,
正死死抓着她的头发。谢玲烦躁地抓了抓头,对着朋友抱怨,“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老掉头发,还头疼。”我收回目光,默默退回了后厨。心脏在胸腔里平静地跳动。当晚,
本地新闻推送了一条快讯。谢氏集团旗下远洋货轮在公海遭遇风暴,沉没,损失惨重。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谢氏集团”四个字,面无表情地继续吃我的泡面。手机震了一下。
是谢玲发来的微信。陆寻你这个贱人!是不是你搞的鬼!你滚了还要给我们家带来厄运!
你就是个灾星!扫把星!她的头像在对话框上方疯狂跳动。我静静地看着,
然后按下了删除并拉黑。世界清静了。灾星?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第一次,
发自内心地笑了。对,我就是灾星。专克你们谢家人的灾星。3.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换了份工作,在一家花店打杂。每天与花草为伴,日子清净许多。
我的“眼睛”也越来越“好用”。我能看到店里哪盆花快死了,提前把它抢救回来。
也能看到哪个客人最近运势不好,善意地提醒一句“出门小心”。花店老板很喜欢我,
给我涨了工资。我用涨的工资,给我妈的牌位前换上了最新鲜的百合。这天,
店里来了个小姑娘,非要订九百九十九朵黑玫瑰。我看着她身上那浓得化不开的桃花煞,
劝她换成白玫瑰。她不听,还觉得我晦气。结果第二天,她哭着跑来,说她男朋友劈腿了,
对象是她亲闺蜜。从那以后,我在附近一带便有了个“寻半仙”的外号。我对此不置可否。
这天,我在整理花材时,看到了娱乐版头条。
谢氏集团公子谢予舟与首富千金白若曦下月订婚,强强联合力挽狂澜?照片上,
谢予舟西装革履,但掩不住一脸的憔悴。而他身边的白若曦,珠光宝气,笑得春风得意。
我的目光落在了白若曦的身后。那个血肉模糊的婴灵,比我上次“看见”时更清晰了。
它像个背后灵,紧紧贴在白若曦的背上,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死死盯着镜头前的谢予舟。
它在笑。无声又诡异。而谢予舟,他头顶的黑气已经浓郁到形成了一个漩涡。
无数惨白的手从漩涡里伸出来,抓着他的头,他的脸,他的脖子。难怪他憔悴成那样。
我关掉手机,继续修剪我的花枝。下午,一个许久不联系的大学同学忽然给我打电话。
“陆寻,周末同学聚会,你来吗?”“不了。”“别啊,来吧,谢予舟也会来,
他最近老跟我们打听你呢。”同学的语气带着一丝暧昧的试探。打听我?
我看了看窗外晴朗的天空。恐怕不是想旧情复燃,是想抓我这个“灾星”回去祭天吧。
“我说了,我不去。”我直接挂了电话。可我没想到,麻烦会主动找上门。4.周六,
我被老板派去给一个大客户送花。地点是一家高级会所。我抱着巨大的花束走进包厢时,
愣住了。里面坐着一群熟悉的面孔,正是我的那帮大学同学。主位上,
谢予舟和白若曦并肩而坐。整个包厢里的人都看见了我。“陆寻?”一个同学惊讶地开口,
“你怎么……”我穿着花店的廉价工作服,和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同学聚会是假,
这根本就是个鸿门宴。是他们故意把地址写成这里,让老板派我过来的。
谢予舟的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他比照片上更憔悴,眼下的乌青浓重,整个人瘦了一圈。
他身上的黑气翻涌着,那些惨白的手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噬。他站起身,想朝我走过来。
“阿舟。”白若曦轻轻开口,按住了他的手。她的笑容依旧完美无瑕,但看着我的眼神,
带着一丝审视和敌意。我没理会他们,径直把花束放在预订的桌上,转身就走。“站住。
”谢予舟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陆寻,我们谈谈。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是不是你?”他固执地问,“我们家最近出的所有事,
是不是都跟你有关?”包厢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我终于转过身,对上他的眼睛。
我的视线越过他,落在他身后的白若曦身上。我看着白若曦,然后,我的目光缓缓下移,
落在了她身后,那个婴灵所在的位置。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
它缓缓地,缓缓地,转过了它那没有五官的头。黑洞洞的“眼睛”,对上了我的视线。
一直带着完美笑容的白若曦,脸上的表情,第一次裂开了一丝缝隙。她抓着谢予舟胳膊的手,
不自觉地收紧了。“阿舟,我们走吧,我有点不舒服。”她的声音有些发颤。谢予舟没有动。
他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从愤怒,慢慢变成了困惑,最后化为一丝恐惧。
“你……看见了什么?”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我没回答。
我只是看着他,看着他头顶那翻涌的黑气,笑了。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猛地推开。
谢予舟的母亲,周岚,一脸怒容地冲了进来。她比上次我在新闻里看到时更加苍老,
两鬓都见了白发。她身上的黑气,几乎凝成了实质,像一件厚重的黑色斗篷,
将她裹得密不透风。她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我面前,扬手就要打我。我侧身躲过。她扑了个空,
更加愤怒。“陆寻!你这个扫把星!你到底对我们家做了什么!”她尖叫着,声音凄厉。
她从爱马仕的包里掏出一本支票簿,撕下一张,狠狠砸在我脸上。“说!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你才肯放过我们家!”支票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我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一串零。
一百万。我看着她那张因愤怒和恐惧而扭曲的脸。一只惨白的手,正从她身后的黑气中伸出,
狠狠捏着她的脸颊,将她的嘴角向下拉扯。我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周岚愣住了。
“你笑什么!”“我笑你,”我弯腰,捡起那张支票,在指尖把玩,“死到临头,
还以为钱是万能的。”我的话音刚落,包厢里的灯闪烁了一下,灭了。一片黑暗中,
女同学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只有我知道,这不是跳闸。是那个婴灵,
它的情绪波动影响到了周遭的磁场。灯很快又亮了。周岚的脸色已经惨白如纸。她看着我,
像是看着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谢予舟快步走过来,扶住他摇摇欲坠的母亲。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陆寻,”他再次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求你,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白若曦也走了过来,她挽着谢予舟的胳膊,身体紧紧贴着他,
像是要从他身上汲取力量。她的脸色同样不好看,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忌惮。“阿舟,
别听她胡说八道,她就是想吓唬我们,想讹钱。”她的话提醒了周岚。周岚指着我,
色厉内荏地吼道:“你敢耍我们!我告诉你陆寻,我能让你净身出户,
就能让你在这座城市里待不下去!”我看着他们一家人。看着他们身后那些翻涌的黑气,
和那个越来越清晰的婴灵。我将手里的支票,缓缓撕成两半,然后是四半,八半。
纸屑从我指尖飘落。“谢予舟,”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开口,“当初是你说的,我是灾星,
白若曦是你的福星。”“现在,你的福星就在你身边。”“你来求我这个灾星做什么?
”5.我的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抽在谢予舟和白若曦的脸上。白若曦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抓着谢予舟的手臂指节泛白。谢予舟的嘴唇翕动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身后的黑气翻涌得更加厉害,那些惨白的手,仿佛要从他皮肤里钻出来。“你!
”周岚气得浑身发抖,“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妈!”谢予舟忽然打断她,
他死死盯着我,“陆寻,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回事,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我看着他眼里的红血丝,和他身边一脸紧张的白若曦。“我的条件很简单,”我慢慢说,
“让她,滚。”我指着白若曦。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白若曦身上。白若曦的身体僵住了。
她身后的婴灵,黑洞洞的眼睛里,似乎流露出了一丝怨毒。
“阿舟……”白若曦的声音带着哭腔,柔弱地靠在谢予舟身上,
“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陆小姐,她要这么针对我。”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过去七年,
我见了无数次。每一次,谢予舟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她。这一次,他却迟疑了。
他看着我,又看看怀里的白若曦,脸上满是挣扎。最终,他艰难地开口:“陆寻,
若曦她是无辜的,你别……”“是吗?”我打断他,笑意更冷,“那你们就好好锁死,
祝你们百年好合,断子绝孙。”说完,我不再看他们,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周岚气急败坏的咒骂和白若曦压抑的哭声。我头也没回。走出那家会所,
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我的手机响了,是花店老板。
她在那头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回事,说客户投诉我态度恶劣,要求开除我。“我知道了,
张姐,给你添麻烦了,我等下就回去办离职。”我平静地挂了电话。意料之中的事。
我沿着马路慢慢地走,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难过。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谢予舟,
这就是你的选择。很好。接下来几天,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为周岚的“封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