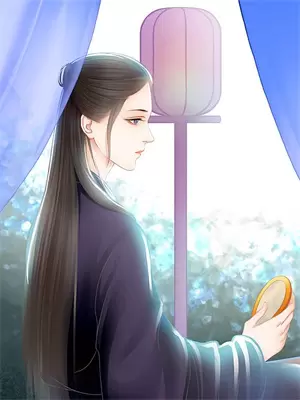第一章 被吃掉的春天我醒来的时候,月亮正挂在山脊的豁口,
像一枚被啃噬得只剩半边的糖块,泛着一种不祥的、黏腻的惨白光泽。风从松林里钻出来,
带着湿冷的甜腥,一下一下拍在我脸上,那气味像是腐烂的花蜜混合了铁锈,钻进鼻腔,
勾起一阵生理性的厌恶。我下意识去摸手机——冰凉的机身沉默着,屏幕是彻底的黑,
像一块烧尽的炭,无论怎么按压电源键,都没有丝毫反应。指尖传来的只有绝望的死寂。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勉强辨认周遭。没有路,也没有回头路,
只有一条被浓密苔藓和暗色藤蔓吞没的石阶,歪歪扭扭,斜斜地插进下方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像某人故意留给我的、一条嘲弄而沉默的舌头。头痛欲裂,记忆的碎片如同沉船后的漂浮物。
我清晰地记得,那列绿皮火车是在下午两点零八分,准时碾过锈迹斑斑的铁轨,
驶入我那偏僻故乡的陈旧站台的;记得林默老师——我初中时的历史老师,
也是这次叫我回来的缘由——在出站口等着我,他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眼袋深重,
递给我一支廉价的本地卷烟,烟雾呛人,
我没接;记得自己把那个轻便的行李箱扔进他那辆破旧皮卡的后备厢时,箱轮磕在金属边缘,
发出一声类似呜咽的、短促而古怪的怪响。再往后呢?记忆就像被谁恶意抽了帧的电影胶片,
突兀地跳片,
刺眼的白光和滋滋的杂音——我究竟是怎样穿过那座死气沉沉、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的镇子?
怎样跨过那条在记忆中夏日汹涌、此刻却覆盖着一层不自然薄冰的河流?
怎样踩过镇子西边那片荒芜的、连墓碑都仿佛在瑟缩的坟坡?最终,
是怎样抵达这座我自幼便被长辈告诫“永远不要主动靠近”的、笼罩在传说与禁忌中的东山?
答案被硬生生挖走了,只在脑海里留下一个空洞的、仿佛还在汩汩流血的窟窿。
一种冰冷的恐惧,并非源于未知,而是源于这种被精准剥夺的已知,顺着脊椎慢慢爬升。
但我清楚地知道,并且这种认知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确定性:春天不见了。
不是气候学上的延迟,不是诗人笔下伤春悲秋的比喻,更不是我精神恍惚的错觉。
而是把“春天”这个概念,当成一整块透明、冰凉、带着梨花和青草香味的巨大果冻,
被人连带着承载它的盆子,一起从这个世界里端走了。
空气里没有任何植物萌发、花朵绽放的鲜活气味,
土壤里没有蚯蚓翻动、昆虫蠕动的生命迹象,
连头顶稀疏的星光都透着一股隔夜的、令人作呕的馊味。我伸出手,徒劳地在空气中抓挠,
只抓到一把像死人指甲般干脆、冰冷的寒风。那一刻,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死寂中无限放大——咚、咚、咚——沉闷,规律,却毫无生气,
像是一个被遗忘在空房间里的人,用尽最后力气敲打着墙壁,提醒我:你还活着,呼吸着,
可你存在的根基,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某个重要部分,已经被彻底开除。我必须走下去,
沿着这条苔藓舌头指引的方向。或许答案,就在石阶尽头那片更深的黑暗里。
第二章 舌头做的地图石阶的尽头,是一处开阔但破败的采石场旧址。
月光在这里似乎变得稍微慷慨了些,照亮了那些被人工劈开、又历经风雨侵蚀的巨岩剖面。
岩石断面泛着一种诡异的幽蓝色,不像石头,
更像是一瓣瓣被强行掰开、暴露在空气中的巨大肝脏,纹理间仿佛还残留着生命的湿润感。
采石场中央低陷处,积着一潭死水,水面上漂满了枯黄的松针,密密麻麻,
几乎覆盖了整个水面,奇怪的是,如此清澈的月光下,水面却映不出我的倒影,
只有一片空洞的黑暗。一种莫名的牵引力让我蹲下身,试探着将手伸进潭水中。水是温的,
触感滑腻得令人不适,带着一股浓郁的生铁腥气,仿佛浸泡过无数锈蚀的刀剑。更诡异的是,
当我掬起一捧水,指缝间漏下的液体竟拉出了细长、透明的丝絮,像潮湿天气里生长的菌丝,
又像是婴儿刚剪下、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脐带,在空中微微摇曳。我本能地俯身干呕,
胃部剧烈抽搐,却什么也吐不出来。胃里空得发慌,只剩下一种坚硬的坠胀感,
那是一枚冰冷的硬块,在腹腔内上下滚动——我恍惚想起,
在火车经过那段漫长的东山隧道时,
突如其来的黑暗和压抑感让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如今,
那口被吞下的黑暗似乎在里面长大了,长出了手脚,化为了一个活物,
在我体内焦躁地来回踱步,寻找着出口。“咔嗒”。
一声清晰的、类似机关转动的轻响从我身后传来。我猛地回头。采石场边缘,
一块看起来与周围无异、饱经风霜的石灰岩,此刻正悄无声息地向内滑开,
露出了一个仅容一人钻入的黑黢黢的洞口。洞壁并非天然岩石,上面布满了深刻的抓痕,
痕里嵌着某种暗红色的碎屑,在月光下闪着油腻的光,像被岁月风干的肉末。
一股更浓烈、更复杂的甜腥气味从洞中涌出,
茶的苦涩、少女发梢残留的石榴香波味——所有本应在温暖四月里出现的、令人愉悦的气味,
此刻被压缩、扭曲成一条湿漉漉的、无形的舌头,从洞口伸出来,对着我,
充满诱惑又带着威胁地勾了勾。没有退路了。我深吸一口那令人作呕的香气,弯腰钻了进去。
洞内并非一片漆黑,一种微弱的、仿佛源自岩石本身的磷光提供了些许照明。每一步落下,
鞋底都会踩碎某种铺满地面的脆片,发出“嚓嚓”的轻响,那声音不像踩碎枯枝,
更像是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窃笑。就在这时,一直黑屏的手机突然自动亮起,
惨白的光芒刺破黑暗。屏幕自动解锁,打开了备忘录界面,
光标在空白的页面顶端急促地闪动着,像在无声地催促我记录遗言。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向屏幕,屏幕如镜,
倒映出的却不是我的脸——那是一张被拉长、扭曲、平滑得没有五官的脸,
像被滚热蜡油彻底封住,只有一个人脸的轮廓。它对着我,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
屏幕“啪”的一声轻响,炸开无数蛛网般的裂纹,光芒彻底熄灭,手机恢复成冰冷的死物。
黑暗瞬间拥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眼球上,几乎让我窒息。在一片绝对的寂静中,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被剥离出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自问自答,空洞而陌生——“谁吃了春天?
”“吃春天的人,也吃记忆。”“记忆被吃完后,我是谁?”“你是剩下的包装纸。
”第三章 林老师不知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了多久,时间感在这里已经完全错乱。
就在我感觉肺部快要被那甜腥气息填满时,前方出现了一点飘忽不定的绿光,
像一只被水稀释过的、奄奄一息的萤火虫。我踉跄着靠近,
发现那是一架老掉牙的旧式铁路信号灯,灯体锈蚀严重,歪倒在冰冷的泥地里。
灯罩已经裂开,裂缝处缠绕着一缕缕纠结的、油腻的黑色长发。而灯柄上,
用磨损的皮绳挂着一张塑封的工牌——“东山线·巡道工·周之同”。我脑子“嗡”的一声,
像是被重锤击中。周之同,是我姐夫的名字!十年前,
他还是铁路段上一名认真负责的巡道工,
却突然因“擅自封闭东山隧道口、导致一列货运列车晚点长达七小时”而被严厉开除,
此后只能在镇上的修车厂打零工,郁郁寡欢,再没穿过那身象征责任的制服。
家里人对这件事讳莫如深,每次问起,都只含糊地说“他撞了邪”,“脑子不清醒了”。
直到去年除夕,他喝多了劣质白酒,拉着我躲在厨房角落,
眼睛通红地嘀咕:“隧道里……有东西……在轨枕下面产卵,白色的,
一簇一簇……”话没说完,就被闻声而来的舅舅当众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骂他“又发疯”。
此刻,他的工牌却出现在这山腹深处,像一枚被精心投递、指向明确的邮票,
散发着不祥的气息。那盏破旧的信号灯开始忽明忽暗,每一次闪烁,
都在潮湿的地面上投下一圈圈扭曲蠕动的阴影——那影子不像任何已知生物,
轮廓像是巨型的蝌蚪,但摆动的尾巴末端,却分明连接着模糊的人脚形状。我屏住呼吸,
数到第七次闪烁时,地面上所有的阴影猛地集体“抬头”,虽然没有五官,
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它们“看”向了我,
同时发出一种尖锐的、混合着婴儿啼哭和老式列车汽笛的诡异声响。与此同时,
一只冰冷、布满粗硬老茧和浓重机油味的手,悄无声息地贴上了我的后背。“小洵,别回头。
”是姐夫周之同的声音!但这声音干涩沙哑,像被粗糙的砂纸反复打磨过,
带着铁锈的颗粒感。我全身肌肉瞬间僵硬,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后颈皮肤上,
滚烫,但几乎在瞬间就冷却、凝固,结成一只钢镚大小的、硬邦邦的痂。
姐夫的声音继续响起,语速极快,
仿佛在抢夺最后一班下行车的登车时间——“它们把季节当罐头,先吃春天,因为春天最嫩,
味道最好。接着是夏天,秋天……等到冬天,罐头盒里空了,翻过来,
就把我们这些人当残渣倒进去涮一涮,榨干最后一点味道。你以为自己只是放假回家,
其实从你踏上归途的那一刻,车票背面早就被盖上了‘副食品’的蓝戳。”“谁在吃?
它们到底是什么?”我强忍着回头和逃跑的冲动,从牙缝里挤出问题。姐夫没有回答。
他只是猛地将一张皱巴巴、带着浓重机油味的纸条硬塞进我外套口袋,然后用力推了我一把。
力道之大,让我毫无防备地向前扑倒,脸重重埋进一滩冰凉滑腻的腐殖质中,
嘴里充满了泥土和腐烂植物的味道。我挣扎着抬头,抹掉脸上的污秽,
再看向身后——空无一人。只有那盏信号灯,在我眼前“啪”的一声爆裂,最后的绿火溅开,
如同黑暗中一簇被无情踩烂的、闪烁着微光的萤火虫尸体。惊魂未定中,
我颤抖着手摸出口袋里的纸条。纸质粗糙,
上面用某种暗红色的、像是凝固血液的物质写着三行歪歪扭扭的字:想不起来的,
就永远别想起。如果非要想起,就去坟坡第三排左数第七座,把碑上的名字擦掉。
记住,用左手。第四章 坟坡我几乎是连滚爬爬地从那诡异的洞口逃了出来。
外面天已微亮,但并非正常的、充满希望的鱼肚白,
而是一种沉闷的、像是掺入了变质牛奶的灰白色,压抑地笼罩着天地。远处的东山轮廓模糊,
像一头被抽掉了所有骨头的巨兽,软绵绵地伏在地平线上,散发着无声的威胁。
我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一路几乎是滑着下了山,凭借记忆中的方向,
径直往镇子西边的坟坡走去。熟悉的镇子此刻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死寂。没有犬吠,
没有鸡鸣,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冰冷地矗立着,没有一丝炊烟。唯一的声响,
是我那个可怜的行李箱拖轮,在水泥路面上刮擦出的单调而刺耳的长音——那声音听起来,
像极了给一具巨大的尸体缝合伤口时,针线穿过僵硬皮肉发出的线脚声。坟坡到了。
一座座灰白的墓碑如同沉默的士兵,排列在荒凉的山坡上。我按照纸条的指示,找到第三排,
左数第七座墓碑。那是一座异常光滑的黑色石碑,材质不明,碑面上一个字也没有,
光可鉴人。我凑近看去,碑面隐约映出我的轮廓,但诡异的是,那倒影清晰,
却唯独缺少了左眼的部分,那里是一片空白,仿佛我天生就没有左眼。我深吸一口气,
回忆起纸条上的话,伸出左手,用指尖去擦拭那光滑的碑面。指尖刚触碰到冰冷石碑,
墓碑内部突然传出“咔哒”一声轻响,清晰得如同老式相机的快门声。紧接着,
整座墓碑如同一个设计精巧的活板门,毫无预兆地向下猛地翻开!我猝不及防,
惊叫着坠入下方无边的黑暗。短暂的失重感后,我重重摔落在坚硬的地面上,尘土飞扬。
咳嗽着爬起来,发现自己身处一条显然已被废弃多年的地铁隧道中。
墙壁贴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现在已经斑驳脱落的绿色马赛克墙砖,残存的广告纸上,
还能依稀辨认出“实行计划生育,促进家庭幸福”的褪色标语。轨道早已锈蚀,
中间停着一列通勤车,车身的红漆剥落,露出底下深褐色的铁锈,
所有车窗都被一种不透明的黑色薄膜从里面糊得严严实实。车厢门诡异地敞开着,
像四片因无法闭合而僵硬的、绝望的嘴唇。我迟疑地走进最近的一节车厢。
脚下传来“咔嚓”的脆响,低头看去,地板上竟然铺满了厚厚一层明信片。拾起几张,
发现全是同一幅画面:一树梨花在阳光下怒放,绚烂得近乎虚假,
花下站着身穿小学六年级校服、表情懵懂的“我”,以及一个站在“我”身旁,
脸部被某种水渍晕染开、完全无法辨认的人影。翻到明信片背面,无一例外,
只用娟秀的字体写着一行字——如果春天被吃掉,你会回来吗?落款日期,
清晰地印着:2013.4.5。2013年4月5日……我十二岁,小学六年级。
那年春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前往东山的春游。而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感冒”而缺席,
在家昏昏沉沉地躺了整整三天。等我康复返校,参加春游的同学们都已经回来了,
但每个人脸上都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呈现出一种统一的、病态的煞白,
并且对所有关于春游的事情闭口不谈,仿佛共同守护着一个可怕的秘密。不久后,
原来的班主任突然辞职,传言说是“精神崩溃了”。新接任的老师在上第一堂课时,
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东山禁入区”五个大字,并且让我们每人画一幅“最害怕的东西”。
其他同学画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自己当时用黑色的蜡笔,
画了一棵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的梨树,扭曲的枝桠上,
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形状的人耳朵。此刻,这些印着梨花的明信片,
像一层厚厚的、冰冷的积雪,铺满了车厢。每一脚踩下去,都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仿佛踩碎了无数昆虫的甲壳,
同时溅起一股浓郁到令人头晕的、陈年梨花的 artificial 香精气味。
这股熟悉又陌生的花香,像无数细小的、带着倒钩的虫子,拼命钻进我的鼻腔,
直冲大脑深处,
我自身潜意识强行遗忘的胶片——闪回:2013.4.5·东山·梨树林十二岁的我,
其实并没有感冒。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动让我偷偷溜出了家门。
我骑着自行车,凭着模糊的直觉,竟然一路尾随着学校的包车,来到了东山的背后,
一片我从未涉足过的、开满诡异梨花的山谷。我躲在茂密的灌木丛后,
看见同学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围成一个松散圆圈。圆圈中央,
摆着一口我在老式澡堂里见过的那种、硕大的铝制浴盆。
盆里盛满了某种透明、微微颤动的胶状物,在稀疏的阳光下,反射着油腻的光,
像一块硕大无朋、等待被分食的果冻。然后,
我看到当时的班主任——那位总是很温柔的林默老师——拿起一个白色的搪瓷缸,
带头从浴盆里舀起那“果冻”,分发给排着队的孩子们。孩子们接过缸子,没有丝毫犹豫,
低头吃得非常香甜,嘴角甚至溢出了淡粉色的、黏稠的汁水。轮到我了。不知何时,
我也排进了队伍。当我走到浴盆前,伸出手,林老师却突然按住了搪瓷缸。他抬起头,
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平日的温和,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机械的审视。他说:“周洵,
你没有票。”我愣住了,下意识地质问:“什么票?春游不是大家都交钱了吗?
”林老师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我的胸口。我低头,骇然发现,
自己胸前的衣服上,不知何时被盖了一个清晰的蓝色印章,像市场里检验猪肉的合格章,
上面写着:副食品·不合格。下一秒,地面剧烈震动、裂开,
那口铝制浴盆猛地向下沉去。周围的梨树成排地、无声地倒塌,仿佛只是舞台上虚假的布景。
布景之后,露出了隐藏在后面的“东西”——我无法用任何已知的词汇描述它的形态,
只能说,它像一条由无数张痛苦、麻木、扭曲的人脸缝合而成的、巨大无比的舌头,
舌苔上布满味蕾般的凸起。那舌尖,
正卷着一团模糊的、散发着春日气息的光晕——那分明是整个四月的气息和景象!
舌头正一点点地、缓慢地缩回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心裂口。我的同学们,包括林老师,
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黏在了那条巨大的舌头上,双脚离地,身体僵硬,
但他们却齐刷刷地转过头,面向着我,脸上露出完全一致的、空洞而诡异的笑容,
齐声喊道:“下周见!”无边的恐惧攫住了我,我转身想跑,脚下却踢到了一个硬物,
发出“咣当”一声脆响。低头一看,是那只白色的搪瓷缸,它滚落到我的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