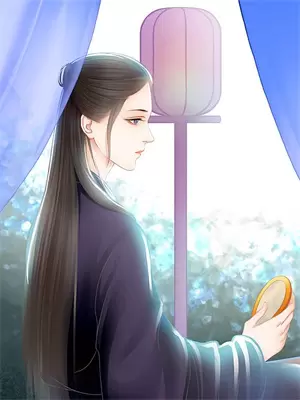规则怪谈降临后,我被关进了青山精神病院。陈医生坚持说我产生了幻觉,需要药物治疗。
我盯着他身后,冷静地开口:“你带来的那个没脸的护士姐姐,正在舔你的脖子。
”他强装镇定,呵斥我胡说八道。 可当他给我注射镇定剂时,针管对我毫无效果。“医生,
你被污染了,”我轻声告诉他,“我才是医生,而你……需要治疗。”当晚,
陈医生的尖叫响彻病房。 第二天,他穿着病号服,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
我们“治疗”了全院医护,组建了一支“疯子军团”。直到我撕碎那本污染源病例簿,
所有幻觉瞬间消失。医院大门打开,一群黑衣人恭敬站立:“专家,
下一个城市需要您的‘治疗’。”第1章 错误诊断我叫林辰,
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现在,青山精神病院三楼的这间诊室里,
冷白的灯光明明晃晃,照着一尘不染的桌面,也照着坐在我对面,穿着白大褂,
一脸严肃的陈启明医生。以及,他身后那个。
它穿着和外面走廊里护士们同款的淡粉色护士服,裙摆及膝,脚下是一双白色的护士鞋。
但没有脸。本该是五官的位置,是一片光滑的、如同剥壳鸡蛋般的皮肤。
它就那样安静地站在陈医生椅背后方的阴影里,微微佝偻着身子,
湿漉漉的、暗红色的长舌头,正从那张并不存在的“嘴”里伸出来,一舔,一舔,
缓慢地刮过陈医生裸露在衣领外的脖颈皮肤。陈医生毫无所觉,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镜片后的眉头紧锁,低头看着手里的病历夹。“林辰,男,二十三岁。
主诉:持续一周声称看到‘不存在的人影’及‘规则性提示’,伴有强烈的被害妄想,
拒绝进食,认为食物被污染……”他念到这里,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我,
“能具体描述一下你看到的‘人影’吗?比如,它们长什么样子?”我靠在坚硬的椅背上,
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这里的规矩很重要,我知道。不能激怒它们,
不能表现出过度的恐惧,也不能……试图去说服那些已经被“污染”的人。“陈医生,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你带来的这位护士姐姐,
好像有点……特别。”陈医生的笔尖在病历纸上顿了一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再次抬眼,
眼神里带着职业性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林先生,这里只有我和你。
没有第三个人。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产生了幻视。”那条暗红色的舌头又一次舔过,
留下湿腻的反光。无脸护士的头颅歪了歪,那空无一物的“脸”似乎转向了我。
我轻轻吸了口气,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刺鼻,
几乎盖不住那东西身上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腐朽气息。“她没有脸,陈医生。而且,
她正在舔你的脖子。”诊室里死寂了一瞬。咔哒。陈医生合上了手中的钢笔帽,
动作有些僵硬。他放在桌面上的左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但他很快控制住了,
脸上甚至挤出一个堪称“和蔼”的专业笑容,只是那笑容并未抵达眼底。“林辰,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感知觉障碍,在精神分裂症早期……”“她的舌头是暗红色的,很湿,
上面好像还有细小的倒刺。”我打断他,目光牢牢锁住他身后那片虚无的阴影,
“你的脖子右侧,衣领下面,现在是不是感觉有点黏,还有点凉?
”陈医生的喉结不受控制地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抬起来,
想要去摸自己的脖颈,但在半空中硬生生停住了。他深吸一口气,脸色沉了下来,语气加重,
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够了!林辰,你这是典型的幻觉!并且伴有强烈的现实扭曲力场,
试图将你的妄想强加于人!你必须接受治疗!”他猛地站起身,白大褂带起一阵风。
他按下了桌角的呼叫铃。“你需要镇定,需要药物控制!这是为你好!”门被推开,
进来的是两个穿着蓝色护工服、身材高大的男人,面无表情,眼神麻木。
他们一左一右站到我身边,像两座铁塔。他们的头顶,
各自盘旋着一团模糊的、不断扭曲变化的灰色雾气,像是有无数细小的虫子在雾气中蠕动。
这是被轻度污染的迹象,还不严重,但足以让他们失去大部分自主思考能力,
变成遵循“规则”的行尸走肉。“带他去三号处置室。”陈医生挥了挥手,重新坐下,
拿起笔,似乎想继续写病历,但笔尖悬在纸面上,久久没有落下。我没有挣扎。
挣扎是徒劳的,还会提前触犯某些“规则”。我只是在被架起来的时候,
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无脸护士。它依旧站在那里,舌头缩了回去,
那片光滑的“脸”正对着陈医生微微颤抖的背影。处置室比诊室更冷,
墙壁是那种令人压抑的淡绿色。我被固定在一张冰冷的金属椅子上,
皮带勒紧了我的手腕和脚踝。空气里弥漫着更浓的药水味,还有一种……铁锈般的甜腥气。
陈医生跟了进来,他已经恢复了镇定,手里拿着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针管和一小瓶透明的药剂。灯光下,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眼袋很深。
“这是强效镇定剂,林辰。”他一边用酒精棉擦拭着我的手臂皮肤,一边用那种刻意放柔,
实则毫无温度的语调说着,“它会让你好好睡一觉,醒来后,
那些乱七八糟的幻觉就会减轻很多。放轻松……”冰凉的酒精棉擦过皮肤,
激起一阵鸡皮疙瘩。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向处置室门口。那个无脸护士,
不知何时也跟来了。它就站在门框的阴影里,悄无声息。这一次,它没有舔舐,
只是“注视”着这边。那空无一物的凝视,比任何恶毒的眼神都让人心底发毛。
针尖闪着寒光,刺破了我的皮肤。冰凉的药液被缓缓推入静脉。陈医生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似乎在期待着我眼神涣散、陷入沉睡的那一刻。一秒,两秒,三秒……我们就这样对视着。
他眼中的期待,逐渐变成了疑惑,然后是难以置信。我眨了眨眼,
清晰地感受着药物在血管里流动的凉意,但它们就像滴入沙漠的水滴,瞬间消失无踪,
没有带来丝毫困倦或意识模糊。我的大脑异常清醒,
甚至能清晰地“看”到那药液进入我身体后,被某种无形的力量迅速分解、湮灭的过程。
“看来你的药,”我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处置室里格外清晰,“对我没用。
”陈医生的手猛地一抖,针头差点脱手。他像是被烫到一样,飞快地拔出了针管,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手里的空针管,嘴唇哆嗦着:“不……不可能!
这剂量足够放倒一头牛!”他身后的无脸护士,似乎往前挪动了一小步。
那团灰色的、没有五官的平面,给人一种它在“好奇”的错觉。
我看着他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看着他眼神里第一次浮现出的、属于人类本身的惊疑和恐惧,
推翻了他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专业知识和理性认知。是时候了。我调整了一下被束缚的姿势,
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然后迎上他慌乱的目光,用一种近乎耳语,
却又带着奇异穿透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陈医生,你还没明白吗?”“你,
被‘认知污染’了。”“我,才是这里唯一的医生。”“而你,
还有外面那些……”我的视线扫过门口那两个头顶盘旋灰雾的护工,
最后落回陈医生惨白的脸上,“……你们,才是需要被治疗的病人。
”陈医生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僵在原地,瞳孔因极度震惊而收缩。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却只发出嗬嗬的气音。他手中的空针管,“啪嗒”一声,掉在了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
发出清脆的回响。处置室里,只剩下我们粗重不一的呼吸声,以及那个站在门口阴影里,
无声无息的“护士姐姐”。当晚,深夜。尖锐到变形的惨叫声,
猛地撕破了精神病院住院区的死寂。那声音充满了极致恐惧,几乎不似人声。声音的来源,
正是医生值班室旁边,属于陈启明医生的那间临时休息室。我躺在三号病房的硬板床上,
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被窗外月光投下的、微微晃动的不规则阴影。那阴影,
像极了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头。惨叫声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像被人扼住了喉咙,戛然而止。
然后,是死一样的寂静。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冰冷的墙壁。“晚安,陈医生。
”我在心里默念,“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窗外的月光,似乎更冷了一些。
第2章 反向治疗陈医生的尖叫声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精神病院夜晚虚假的宁静,
也刺穿了许多东西。第二天早晨,送餐的护工换了一个人。
不再是之前那两个头顶盘旋灰雾的熟面孔,
而是一个眼神更加空洞、动作近乎机械的年轻男人。
他把餐盘“哐当”一声放在我床头的铁柜上,稀粥溅出来几滴,落在斑驳的漆面上。
他头顶的灰雾,颜色似乎深了一些,蠕动的频率也更快了。看来,昨晚的动静,
加剧了某种“扩散”。走廊外比平时更安静,但这种安静里绷着一根弦。
偶尔有穿着白大褂或护士服的身影匆匆走过,都刻意低着头,步履匆忙,像是在躲避什么。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连眼神接触都很少。空气里那股铁锈般的甜腥气,
好像也更浓重了点。我安静地吃完那份寡淡的早餐,坐在床沿,等待着。大约九点钟,
病房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是预想中查房的医生,
而是两个穿着蓝色护工服的男人——还是昨天那两位,但今天,他们脸上没有了那种麻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恐惧和强装镇定的复杂表情。他们一左一右站在门边,没有说话,
只是用一种近乎请示的眼神,看向门外。然后,一个人影慢慢地挪了进来。是陈启明医生。
他换下了那身象征权威和理性的白大褂,穿着和我一样的、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
衣服有些宽大,衬得他更加消瘦。他的头发凌乱,眼窝深陷,里面布满了蛛网般的红血丝。
嘴唇干裂,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灰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神。
昨天那份属于医生的笃定和锐利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无法掩饰的惊惶。
他的眼球微微震颤,视线飘忽,不敢与我对视,却又忍不住一次次飞快地扫过我,
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害怕从我这里看到别的什么东西。
紧紧攥着一个东西——是那个无脸的护士经常出现时佩戴的、一个小小的、银色的护士铭牌,
边缘似乎还有些暗红色的污渍。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仿佛那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或者……是某种证明。他站在离我床铺几步远的地方,脚步虚浮,身体微微佝偻着,
完全没有了昨日挺括的身姿。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每一秒都像拉长的橡皮筋。那两个护工不安地挪动着脚步。陈医生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额头渗出冷汗。终于,他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的声音,
字一个字地挤出来:“它……它昨晚……就在我床边……站了一夜……”他的声音干涩沙哑,
带着明显的颤音。“谁?”我问,语气平淡。他猛地哆嗦了一下,
像是被这个简单的字眼刺伤了。他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立刻垂下,
盯着自己颤抖的脚尖。“那个……那个……”他吞了口唾沫,喉结剧烈滚动,
“……没有脸的……护士……”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气音。“哦。”我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它一般不喜欢说话,只是看着。”陈医生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攥着铭牌的手更紧了。“它……它想干什么?”他抬起头,
眼中是纯粹的、未经任何专业粉饰的恐惧,“林……林先生,
你昨天说的……认知污染……是什么意思?我……我到底怎么了?”“我说了,我才是医生。
”我纠正他,从床沿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身体绷紧,
像是害怕我的靠近。我没有理会他的恐惧,伸出手指,指向他身后空无一物的墙壁:“现在,
那里有什么?”陈医生浑身一僵,脖颈像是生锈的齿轮,
极其缓慢地、带着令人牙酸的迟滞感,一点点转向我手指的方向。
他的瞳孔在转向的过程中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呼吸瞬间停滞,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啊——!”又是一声短促的、被扼在喉咙里的惊叫,他猛地向后踉跄,差点摔倒,
被身后的护工扶住。他指着那面空墙,手指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嘴唇哆嗦着,
却发不出一个清晰的音节。只有大颗大颗的冷汗,从他额角滚落。看来,他也看到了。
也许不是无脸护士,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根飘荡的绳索?一个倒吊的人影?
或者只是一团不断扭曲的色彩?无所谓,本质都一样。“看来‘治疗’起效了。
”我收回手指,语气没有任何波澜,“你的感官正在剥离‘它们’覆盖在上面的伪装,
开始接触到真实。这是好事,陈医生,虽然过程会有点……难受。”他瘫软在护工身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神涣散,仿佛刚才那一眼,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神。我走到窗边,
看着外面被铁栏杆分割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脏掉的抹布。“这座医院,已经病了,
陈医生。病得很重。”我背对着他,缓缓说道,“所谓的规则怪谈,
就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认知扭曲病毒。它修改你们的感知,篡改你们的记忆,
让你们把异常当作正常,把真实当作虚幻。而你们……”我转过身,
目光扫过他和那两个同样面露惧色的护工,“……你们这些原本的医护人员,
是第一批被感染,也是感染最深的重症患者。”陈医生呆呆地看着我,
脸上的恐惧慢慢被一种更深的茫然和崩溃所取代。“那……那怎么办?”他喃喃道,
像个迷路的孩子。“很简单。”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萎靡的样子,
“找到传染源,清除它。或者,在找到之前,先控制住疫情的扩散。
”我指了指门口:“现在,带我去见见其他‘病人’吧。从……张副院长开始怎么样?
我注意到,他头顶的那团‘脏东西’,颜色特别深。”陈医生猛地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张副院长,是这家医院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
也是昨天坚持要对我采取“强制医疗措施”最强硬的一个。但此刻,
陈医生只是犹豫了不到两秒,就用力地点了点头。他扶着护工的手臂,挣扎着站直身体,
虽然依旧颤抖,但眼神里,
已经多了一种东西——一种名为“依赖”或者说“皈依者狂热”的东西。
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病友”,也是我的第一个……跟班。我们走出病房,
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和白色的医生袍形成了诡异的组合。走廊里偶尔遇到的医护人员,
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穿着病号服、神态惊惶却紧跟在我身后的陈医生时,
都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然后匆匆避开,仿佛我们是什么瘟疫源头。他们头顶的灰雾,
或多或少,都在不安地翻涌。我知道,昨晚陈医生的尖叫,和今天他这打败性的转变,
就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已经开始在这座被“污染”的医院里,激起涟漪了。
而我的“反向治疗”,才刚刚开始。下一个,张副院长。我很好奇,当他看到他办公桌后面,
那个一直对着他微笑的、没有影子的“秘书”时,会是什么表情。
第3章 病友成群张副院长的办公室在行政楼顶层,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
吸走了所有脚步声,只剩下一种压抑的寂静。空气里昂贵的香薰味道,
也压不住那股愈发清晰的铁锈甜腥。陈医生跟在我身后半步,呼吸急促,
病号服下的身体仍在微微发抖。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枚护士铭牌,像是握着一枚护身符。
两个护工留在楼梯口,他们的“权限”不足以进入这片区域。“林……林医生,
”陈医生压低声音,喉结滚动,“张副院长他……他的办公室,平时不允许我们随便进的。
”“现在规矩变了。”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向那扇厚重的实木门。门没锁。我推开它。
办公室宽敞明亮,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灰蒙蒙的城市天际线。红木办公桌后,
张副院长正埋首文件,听到动静,不悦地抬起头。他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肥胖的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而充满权威。“陈启明?
”他先是看到了我身后的陈医生,眉头立刻拧紧,语气严厉,“你怎么穿着病号服?
像什么样子!还有你,”他的目光转向我,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审视,“林辰?
谁允许你离开病房的?护工呢!”他作势就要按桌上的呼叫铃。“张副院长,”我开口,
声音不大,却让他按向呼叫铃的手指顿在了半空,“你身后的那位秘书小姐,裙子穿反了。
”张副院长的身体猛地一僵。在他宽大的办公椅侧后方,站着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的“女人”。
她身材窈窕,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姿态标准。但她没有影子——阳光从窗外照进来,
在地毯上投下办公桌、椅子和张副院长清晰的影子,唯独她站立的地方,空空如也。而且,
正如我所说,她身上的套裙,前后是颠倒的,拉链狰狞地裂开在胸前。
张副院长的脸颊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猛地扭头,看向自己身侧的空地——在他眼中,
那里或许真的有一位能干漂亮的秘书随时待命。“胡说八道!”他转回头,脸色涨红,
怒斥道,“我这里没有什么秘书!林辰,你的病情比报告上写的还要严重!
看来常规治疗对你已经没用了!”他彻底按下了呼叫铃。走廊外立刻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之前的两个护工没有出现,进来的是另外三名穿着白色制服、体型更壮硕的男性护工,
他们眼神凶狠,头顶的灰雾几乎凝成了实质,像一团团肮脏的棉絮。“把他给我控制住!